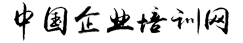作者:佚名 来源于:家长学院
此外,景帝作为武帝的父亲,对其喜好态度影响亦极大。虽然文帝好刑名之言,令“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为景帝的“太子舍人”,而景帝又有“天资刻薄”之名,杀堂弟吴太子、师父晁错全族、功臣周亚夫乃至逼死亲子临江王,百无禁忌,亦颇有法家之风,然细察其喜恶,所钟情者却为儒家。这一点从其对辕固生的爱护中颇可窥得。《史记·儒林列传》载辕固生与黄生之争论,其言语已颇犯忌,而景帝不以为忤。之后辕固生得罪窦太后被令刺豕,景帝特地“假固利兵”,可谓关怀备至。将此与前述景帝阴刻行为相比,对比实不可不谓强烈。
更为明显的是景帝对卫绾的使用,命其为太子太傅,并在在位末年命卫绾为丞相,视为顾命之臣,“以为敦厚可相少主”。而卫绾在建元元年的上书则云:“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其仇视刑名之学的态度跃然纸上,实开独尊儒术之先声。此外,对两汉儒学影响甚大的董仲舒亦是“孝景时为博士”。
《史记》称“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然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景帝朝大臣王臧、文翁、韩婴、晁错皆为儒家,可见景帝朝对儒者已开始悄然重用。其子刘德早在景帝前二年就被封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更有求民间经书,大兴儒学之举,其背后无疑亦当有景帝的支持(参见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
由此看来,儒术之独尊实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非武帝个人心血来潮。
而儒家中庸的特性更使其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的韧性,这一特点使其一旦登顶,就绝难如黄老思想那样被取代。武帝以儒学代替黄老,由无为走向有为,而其身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竟同样可以用儒学批评武帝,使政策转向休养生息。在不更改根本性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转向,此种强大韧性绝非其余诸家所能实现,而其余诸家则不得不为儒学所并,这正是儒家不因帝王一时喜好而倏兴倏衰,能在其后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儒家之基础既已如此雄厚,其所欠者,实仅在于一个勃发的机会,改变“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的状况而已。而自惠帝以来,承平日久,以军功取士的流动体系几乎停滞,朝政被功臣及其后代所把持,亟须新的选官途径。两种需求勃然相激,乃成武帝朝选官制度之大改革。《董仲舒传》称“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儒学既已居主流,又受到武帝支持,则孝廉之举与学校之官为儒家垄断自是必然。这些政策建议对儒学独尊这一历史进程的影响远较其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重要。然将此事全部归功于董氏,恐是儒家后学之溢美。
州郡举孝廉之事,亦发生在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事发生在贤良对策之前,与董仲舒上书或无直接关系。
从后世来看,此荐举制的实施是选官制度上的一大改革。然此令在最初并未引起地方重视,故而在元朔元年,武帝复下诏责不举孝廉之罪。有司议其罪云:“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大约在此之后,荐举制才成为汉廷的重要选官制度。如前所述,自秦以来,儒家在文化部门已居主体,而在武帝支持下,文化教育部门则进一步被儒家所垄断,假以时日,士人阶层皆难脱儒家之教育体系,主流荐举对象自亦非儒家莫属。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以郡为单位举荐人才的方式对时人的社会观念亦产生了影响。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曾指出,《史记》叙述人物之籍贯尚以县为单位,是为战国遗风;而《汉书》叙述人物籍贯则已以郡为单位,体现了时人新的区域观念的建立,是西汉帝国对郡建设的成果。胡先生对这一变化的观察确实到位,然这种变化实非渐变所致。如文中所叙,董仲舒、司马迁等武帝时人尚皆以县为籍贯,然宣帝时萧望之竟已有“东海萧生”之号。时间相距如此之近,而观念悬殊如此,其间自当有突变因素。个人以为,武帝以郡为单位施行荐举制实为影响此观念之主因,自此以后,各郡士人在选官渠道方面形成互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对郡的认同感自会大幅度提升。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上一篇: 唐诗中的“最后一片叶子”
下一篇: 早期《诗经》的形成与编纂
【相关文章】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